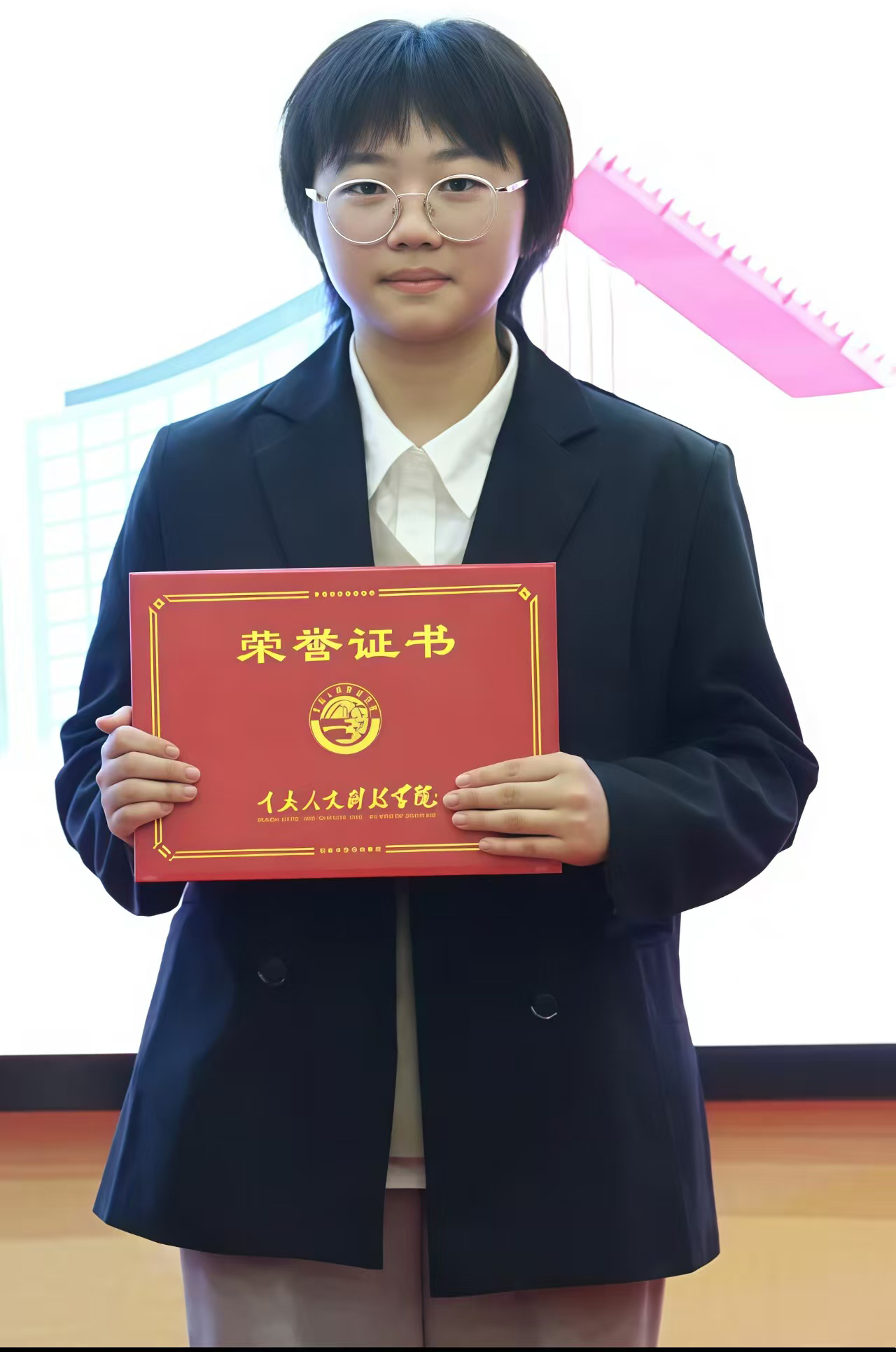品读经典 阅见未来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师生读书征文作品选
|
编者按:为进一步激发阅读热情,推动“书香校园”文化建设,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重庆人文科技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联手重庆作协文学成果转化委员会、重庆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环球人文地理刊系,推出“名家进校园·大师写作课”系列活动,分别邀请臧棣、吉狄马加、杨争光、梁平、叶舟五位文学大家,走进校园,与师生深度交流,读书荐书。并面向全校师生开展“品读经典 阅见未来”征文比赛,晚报夜雨副刊特筛选优秀作品,以飨读者。 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读《红蕖留梦——叶嘉莹谈诗忆往》 杨垒
百年春华间,有这样一位女性,她诗心早慧,却历经磨难,鞠身践行一生,弘扬中国传统诗词文化。她说,“人应有‘弱德之美’,但‘弱德’并不等同‘弱者’,弱者被生活击垮,而具备弱德之美的人,有所承受,更有所坚持,有所承担”。这便是叶嘉莹先生,被誉为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灯人”,中国最后一位“穿裙子的士”。 读叶嘉莹先生的《红蕖留梦》时,心境也如先生笔下的“掬水月在手”般变化。先生于荷月出生而小名荷,十六岁时作诗“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八旬之后赋下“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已老梦偏痴。”在《尔雅》里,荷花也叫芙蓉,菡萏,芙蕖,是先生梦与情的载体,这大概也是作者张侯萍以“红蕖”来作为书引的缘由吧。 在书中,叶嘉莹先生以温和淡雅的语言将一生的重要篇章娓娓道来:满清族人,年少丧母,战乱流离,南下台湾,婚遇不淑,无家可归,中年丧女,但却有幸幼时得家传,年少遇良师,学问贯中西,桃李满天下。“忧患”与“诗词”伴随了先生的一生,她也曾说“我在忧患中走过来的,诗词的研读并不是我追寻的目标,而是我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 轻合卷页,如水的月光滴进我的眼眸,抬手擦拭,却是泪痕斑驳,遗音沧海如能会,便是千秋共此时。叶嘉莹先生于11月24日与世长辞,享年一百岁。她将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国古典诗词,传承文化之美,在学术殿堂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以坚定的信念,谱写了女性的壮丽诗篇。 似月停空,月映千川,人生百岁,先生千古。 (作者就读于工商学院) 若你走近那片群山 ——读《小山和小山之间》 舒露
这本书以母女关系为主题,巧妙编织女儿和妈妈的双视角叙事。一对母女伫立在彼此的山尖对望,山与山之间呼啸而过的,有母性关怀的传承、女性挣扎在命运中的身影、母女羁绊的重塑、回望过去的苍茫和视角差异的比对。 母亲温暖的胸脯,哺育我,环绕我,托举我。王彩英和任蓉蓉,母亲跨越崇洋远赴他乡照顾妊娠期的女儿,母亲的爱与关怀一定是托举起了什么。 如作者自序,“山”指世间所有的母亲。命运的河流淌过此间,母女的羁绊要在汇流中重塑。血脉是母女之间丝缕成线的缠绕,命运的演进,更是将蓉蓉和彩英捆绑,高浓度的爱越过阈值就成了控制,蓉蓉给得太多,彩英逃走了。 长时间的分隔,对母女来说,是喘息的窗口也是和好的契机,于是当她们因为又一个新生命而再次亲密时,命运的云,才从母亲那头飘到女儿这头,下一场相似的雨,水气氤氲山间,在风摇雨打中,跨越时空跨越岁月,读懂我们女性的天命,完成女儿与母亲的——山与山之间的思想汇流。天命,落在我们女人头上,或许从来就不止关于自我,但必须要有自我。 书中这样形容任蓉蓉,“我把脖子伸得长长的,随时都在等着路过的风来决定我的命运”,像不像一朵垂颈的花,吐蕊开放,警惕风的折腰。我虽只是在读两位女性的故事,但有很多感受与自己有关。我在这一对母女的身上,看见了自己和我的家人。花儿,我的那些花儿,如果有来世,要不要孕育在我的溪谷,在那里,我要给你们和风细雨、扶疏绿影,当然还有爱,一如你们给我的那样。 (作者就读于护理学院) 一点绛色,缀点大宋 ——读《李清照词传》有感 湛继辉
若问世间最杰出的女词人是谁?大家脑海里都会想起那位巾帼独秀,“千古第一才女”、易安居士——李清照。 生逢宋代鼎盛时期,又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就对诗词耳濡目染的她,在十六岁时便写下千古传唱的词作,“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年纪轻轻,便能作出名动京城之作,按理来说也够了,但是李清照并没有成为方仲永,反而是愈发勤奋地学习词律。 她爱饮酒,一次小醉后,她写下“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样爱酒但不嗜酒的态度,便可窥见才女的节制与品味。 十八岁的李清照嫁给了赵明诚,他们两情相悦,又志趣相投。她曾用“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寄予远游求学的丈夫。这是什么?这是来自遥远宋代的情书,还是女子写给心仪的男子的情书。 苏轼认为词“自是一体”,可李清照不那么认为,她说,词“别是一家”,并著《词论》,据理力争。她评柳永“词语尘下”;评秦观“少故实”;评黄庭坚“多疵病”。对于苏轼的词,更是直言“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在男性主导的文坛中,李清照能够敢于挑战权威并且坚定不移地捍卫自己的立场,展现出她的自信和坚定。 晚年的她,遭遇了靖康之变。看到丈夫赵明诚面对金人攻城时的弃城而逃,她心中哀凉,写下“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赵明诚病逝后,她尝尽颠沛流离的苦痛,逃难时途经八咏楼,登楼遥望南宋残破的半壁江山,她说,“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 李清照,活得像一个骑士,她的情真意切是真的,她的愁云惨淡是真的,她的通透豁达也是真的。字里行间,品完她的一生,这位“莫道不消魂”的女词人,却有“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作者就读于建筑与设计学院) 挣脱窄门,追寻广阔人生 雷展
小说《窄门》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段纯洁而又痛苦的爱情故事。主人公杰罗姆与阿莉莎相互爱慕,可阿莉莎坚信,只有通过窄门才能到达真正的幸福,她不断地压抑自己的情感,最终在痛苦中孤独地离去。杰罗姆则在失去阿莉莎后,陷入了深深的迷茫和悔恨之中。 他们的爱情是如此的纯粹和美好,却被阿莉莎对窄门的执着所束缚。她认为,只有通过放弃尘世的幸福,才能进入窄门,获得真正的救赎。 阿莉莎相信只有通过窄门才能获得永恒的幸福。这种信仰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她力量和勇气,却也让她变得过于执着和狭隘,把窄门看作是唯一的出路。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会看到一些人因为执着而变得盲目和狭隘。他们把自己的信仰看作是绝对的真理,不容置疑和挑战,忽略了信仰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忽略了人性的弱点和局限性。 《窄门》告诉我们,人生并不是一条笔直的道路,而是充满了曲折和坎坷。同时,人生也不是一场孤独的旅行,需要与他人相互扶持,相互关爱。 我们不能被自己的执念和狭隘所束缚,应该勇敢地面对人生的不确定性,学会接受不完美,在平凡中发现美好。保持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与他人相互扶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走出窄门,追寻广阔的人生。 (作者就读于体育学院) 随风而逝的灵魂与不灭的坚韧 ——《飘》读后有感 颜欢
《飘》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通过细腻的情感描绘和跌宕起伏的情节设置,展现了主人公斯嘉丽那随风而逝却又坚韧不拔的灵魂。这不仅是一部爱情小说,更是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深刻揭示了人性中的善恶、爱恨、忠诚与背叛。 风中的玫瑰:斯嘉丽,一个集美丽、智慧、勇敢于一身的女子,生命如同风中摇曳的玫瑰,既娇艳欲滴,又坚韧不屈。战前,她是任性、骄傲、不拘小节的少女,享受着生活的无忧无虑。然而,战争的爆发,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将她的生活彻底颠覆。 面对家园被毁、亲人离世、生活困顿,斯嘉丽没有选择沉沦,她摘下了昔日的娇弱,换上了坚强的盔甲,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了重建塔拉的重任。她的蜕变,是对“飘”这一主题最生动的诠释——在时代的洪流中,她虽随风飘荡,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方向,不曾迷失。 爱与恨的交织:《飘》中的爱情复杂又深刻。未了的情缘,让人扼腕叹息,但也正是这份遗憾,让《飘》的爱情故事更加真实、动人。它告诉我们,爱情不仅仅是甜蜜的相拥,更是痛苦的磨砺,是在不断的失去与寻找中,学会珍惜与成长。 时代的印记:《飘》不仅仅是一部关于个人命运的小说,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社会的方方面面。通过斯嘉丽一家的遭遇,读者可以窥见战争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巨大影响,无论是经济的崩溃、家庭的破碎,还是人心的动荡,都在小说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 小说也反映了那个时代女性地位的低下与挣扎。斯嘉丽作为女性,不仅要面对战争带来的困境,还要在男权社会中争取自己的立足之地。 《飘》以独特的魅力,跨越了时空,成为了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它不仅讲述了一个女人的成长故事,更是一部关于人性、爱情、历史与命运的深刻思考。斯嘉丽那随风而逝却又坚韧不拔的灵魂,成为了无数读者心中的灯塔,照亮了他们前行的道路。 (作者就读于文新学院) 在苦难中寻生命真谛 ——读《活着》 李芮
主人公福贵是旧时代的“富二代”,他的父亲是地主。可随着一系列社会变革,富贵的一生不得不经历起起落落,从纨绔子弟到穷困潦倒。年少时挥金如土,却在后来的生活里为了一把米而无可奈何。 爹因为他把祖祖辈辈的积蓄拿去还赌债气到最后撒手人寰;娘没钱治病而亡;儿子有庆给领导夫人献血过多殒命;女儿凤霞因病聋哑了,最后生孩子难产而死;妻子家珍因重病缠身离世;女婿二喜被钢筋板压死;唯一的外孙苦根,吃太多撑死了。 这短短百个字就是富贵的一生,他看着身边的亲人一个个离他而去,最后只有这么一头老牛陪着他。 在一个黄昏,太阳缓缓下沉,他不断重复着叫着家人的名字:福贵,家珍,有庆,凤霞,二喜,生怕自己会忘记。这一刻,黄昏不再只是时间的标记,它成了一种情绪,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凄冷和寂寞。最初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因为不得不来。最终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是因为不得不走。 医院那间生离死别的小小屋子是富贵最恐惧的地方,他到过三次这个屋子,也带走了他三次希望,每当希望的火苗刚被擦亮,却在下一秒被掐灭。 书名叫《活着》,所谓“人是为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以外任何事物而活着”。福贵之所以活着,是因为他忍受了命运的不公折磨、忍受生活的残酷无情,忍受人生的无奈孤独,每个亲人的离世都是那么的毫无预兆,措手不及。 小说的结尾,语句平淡如水,却又意味深长——福贵的活着,注定是一种苦难,一种悲哀,他以笑的方式哭,在死的伴随下活着,便是这本书的真谛。 阖上书本之时,世界太过安静,当寂静飘落下来时,盖过人声车声和狗吠,思绪空余间,皆是生命的真谛。 (作者就读于文新学院) 责 编 钟 斌 主 编 陈广庆 策 划 胡万俊 重庆晚报夜雨版面赏析
|
本站论坛的文章由网友自行贴上,文责自负,对于网友的帖文本站均未主动予以提供、组织或修改。
本站对网友所发布未经确证的商业宣传信息、广告信息、要约、要约邀请、承诺以及其他文字表述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等不作任何担保和确认。
因此本站对于网友发布的信息内容不承担任何责任,网友间的任何交易行为与本站无涉。任何网络媒体或传统媒体如需刊用转帖转载,必须注明来源及其原创作者。特此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