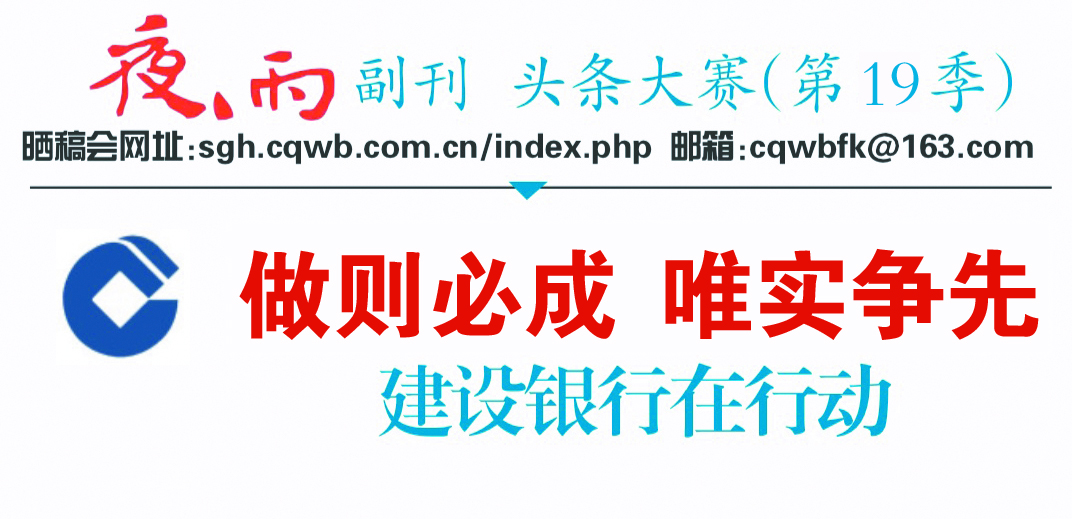夜雨副刊 头条大赛(第19季)|吴天胜:炎炎夏日清凉记
|
炎炎夏日清凉记 文/吴天胜 夏天不请自来,炎热如约而至。 夏日里,地面是热的,空气是热的,甚至迎面的风都是热的。 大黄吐着舌头,趴在树底下,哈哧哈哧喘着粗气;树叶耷拉着脑袋,像被太阳抽了筋似的。我也浑身无力,大概是中暑了,喝下一支藿香正气液,窝在沙发里,吹着空调,任思绪拉回到往昔。 卖冰糕 白天吃过的冰糕意犹未尽,晚上睡觉都在流口水,尤其是那根绿豆冰糕。 卖冰糕的是生产队的一个大小伙子,天生有点生意头脑。每年夏天,都要骑着自行车去卖冰糕,据说也挣了钱。 他卖冰糕有诀窍,早上进一箱冰糕,斜挎在自行车后座,边走边吆喝。天气好的时候,能卖好几箱。有时候进得多了,或者卖得不好的时候,总在傍晚时分往家赶。那个时候,只要看见大小伙子推着自行车过来,必定是还有冰糕没卖完。 有了经验,我们可以很准确地嚷着让父母买冰糕。父母舍不得,一根冰糕要5分钱呢。我们都吵热,父母便说,“一天就喊热,你们自己也去卖冰糕噻,要好多有好多。”说归说,做归做,父母还是给我们几个小孩买了冰糕。 冰糕是绿豆冰糕,含在嘴里能从头凉到脚,从胸前凉到背壳,那份凉爽,难以言表。尤其是那绿豆沙,含在嘴里细细的、软软的、滑滑的、沙沙的、甜甜的、凉凉的,那种感觉,足可以深刻在记忆的硬盘里,只等那炎热的夏天来唤醒。 绿豆冰糕好吃,但毕竟不可多得,一来父母舍不得钱,二来卖冰糕的也不是每天都剩。但父母那天说的话却让我也卖起了冰糕。 家里本来就有一辆自行车,缺的只是进货的渠道而已。母亲向那个大小伙子打听了进冰糕的地点,又准备了一只大泡沫箱,还有一床棉絮。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跟着大小伙子来到进冰糕的地方,以3分钱一根的价格进了50根。他帮我把冰糕整齐地码在泡沫箱里,用棉絮包好,反复叮嘱我不可随意打开棉絮,即便是卖的时候,也要快拿快捂,不然冰糕很快会化掉。然后,我们骑上自行车朝着不同的方向出发了。 我戴着草帽,骑着自行车,逢人便大声吆喝,“冰糕,冰糕,绿豆冰糕——”。天热得要命,我很想躲在树荫下吃根冰糕,但看着满满一箱冰糕却又舍不得,心里巴不得是早点卖完。 或许是应了那句“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生意的。”果然,到了半下午的时候,我那箱冰糕还没卖完,而且越是往后,越是难卖。放了一天的冰糕差不多已变软了,好多人本来想买的,拿起来一看,又不要了。 到天黑的时候,我只能拖着剩下的冰糕回家。父母见没卖完,就告诉我,这时候应该打折,降价卖了。那天没有卖完的冰糕,全家吃了个够。我却怎么也吃不出那种细细的、软软的、滑滑的、沙沙的、甜甜的、凉凉的感觉了。 父母笑着说:“‘裁缝穿不到好衣裳,木匠坐不到好凳子’就是这个道理。”我接嘴说:“卖冰糕的吃不到凉冰糕。” 冰水与凉虾 去往城里的路上,必定会经过一口水井。水井四四方方,比一张八仙桌还大。井水清凉,过往的行人都爱在井边驻足休憩,渴了喝口井水,热了取井水擦把汗,十分舒服。那口水井渐渐地成了地标,名字也变成了“凉水井”。 走到城里时,口干舌燥,那时没有瓶装的矿泉水,只是偶尔会见到街边有卖冰水的。冰水用玻璃杯盛着,杯口再盖了一块方形玻璃,在炎热的夏天是再诱人不过了。 冰水不贵,我却舍不得喝。毕竟它是要钱的呀,况且路上的凉水井敞开了让人喝,一分钱也不要。“城里有什么好,喝水都要钱”,我幼小的心灵对城里产生了一丝不友好。 冰水清凉、沁甜,还有那么一丝丝薄荷味;冰水入口,身上暑热顿消,精神振奋。喝罢冰水,付完2分钱,心中却有不甘,始终认为2分钱贵了,便想着自己回家也要做冰水来喝,而且喝个够。 回到家里,我们挑上水桶,到凉水井担了一挑凉水回去。怎奈身体瘦弱,只能担半挑,路上跌跌撞撞又抛洒不少,到家时,只剩下小半挑。 将冰水倒入碗中,放入几粒糖精,用筷子搅匀,轻轻啜一口,同样清凉、沁甜,只差了一些薄荷味。即使这样,我们也很知足,每人都美美地喝了好几碗。每喝一碗,就觉得是赚了2分钱。 晚上,母亲见了自制的冰水,知道我们是馋了,告诉我们还有一样更好的消暑食品——凉虾。我们便缠着让母亲做。母亲答应了,但要求我们再担些井水回来。 第二天趁天气还不是很热的时候,我们再担回一些井水。这次担水我们有了经验,在水桶里各放一张荷叶,水就不会荡出水桶了。 水挑回去后,母亲将做好的凉虾放在井水里,又熬了一碗红糖水。红糖是我们家自己用甘蔗熬制的,不像白糖或糖精那么金贵。 母亲给我们每人盛上一碗凉虾,又舀上一匙红糖水。褐红色的红糖水,给凉虾披上了一层玲珑的外衣。凉虾晶莹剔透,飘游在碗中,搅动时,好似一尾尾锦鲤在水中游动;舀起时,红糖水滑落,露出洁白的身子,恰似那剥了壳的虾仁。 凉虾入口,软糯Q弹,凉滑无比,比绿豆冰糕还爽,全身暑热顿时烟消云散。 凉席 晚饭后,女人们在灶屋里收拾,男人们则搬来几条长凳,又在长凳上铺上凉床棍,人手一把蒲扇,躺在上面乘凉,这是夏季入睡前的标配。凉床棍是用指头粗细的竹棍捆绑在一排做成的,睡在上面很凉快,却也硌得很。 小孩子一般不睡它。小孩通常睡凉席,更小的小孩甚至是睡簸箕或篮盘。 凉席用竹子织成。织竹席是精细的技术活,父亲不会。我家竹子多,可请篾匠来织凉席。 织凉席须得用一年生,且长得直溜的竹子,太老的竹子划的篾条易折,太嫩的竹子划的篾条没有韧劲。篾匠用锯子将砍下的竹子截成两三米长,刨去青皮,再划成细条,然后用篾刀剥下最外面的一层竹皮。竹皮约三毫米宽,比纸张稍厚,篾匠们称之为篾条。在开始织凉席前,篾匠还要将篾条在两把篾刀固定的刀缝间“梭”一遍,以求得所有的篾条一样宽,这样还可去除篾条上的毛刺。准备好后,篾匠抖动着理顺的那一大束篾条,篾条柔弱无骨,轻摆身姿,像要涅槃的精灵。 篾匠扫开一块平整的空地,取了几根篾条开始织凉席。织凉席是从中间开始,且是斜着织开来。在织的过程中,手艺好的篾匠可在凉席上织出好多花型,比如“恩爱”“鸳鸯”等等。篾匠织凉席的动作很快,根根篾条在手中像丝线一样穿梭,时不时地还要用一根长木条整平、挤紧织好的凉席。织到后来,凉席可见雏形,边上却是参差不齐的篾条,仿若凉席的美髯。最后就是收口,篾匠用一根细绳放在凉席的边上,然后将参差的篾条在细绳处折返回来,将篾条头子再织进凉席中。如此,一张方正的凉席就织好了。 睡觉前,大人将凉席铺在凉床棍上,提前点燃干苦蒿熏走蚊子,再将臂弯中睡着的孩子轻轻地放在凉席上。又用蒲扇在孩子们身上细细地扇出柔柔的风,待到孩子们睡沉后,自己才翻身睡下。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孩子们睡的地方通常会出现一幅汗渍轮廓印。那汗浸透了衣裳,溽湿了凉席,仿若一朵夏花绽放。 凉鞋 小的时候,每到夏天,我都渴望买一双新凉鞋。有了凉鞋就可到处跑了,走沥青路不怕烫脚,走石子路也不怕硌脚。 这个愿望通常能实现,但往往来得较迟。 每年夏天的上半季,都是穿旧凉鞋,多是哥哥剩下的。我不大愿意穿旧凉鞋,它不但旧,而且烂,烂得只能趿着,甚至连拖鞋都不如。 有一次,我穿着旧凉鞋去卖冰糕,太阳毒辣辣地,晒得公路上的沥青都化了,自行车骑在上面很费劲,仿佛总有一股力量在拖拽你。 “冰糕!”一个脆生生、怯生生的叫声引起了我的注意。生意来了!我一个急刹,冰糕箱在自行车后座侧一个趔趄,惯性往前冲,撞得我小腿生疼。我不顾疼痛,跳下自行车,循着声音看去,公路对面一个比我还小的姑娘在朝我招手。 我没有多想,推着自行车就横跨公路。没成想,还没到公路中间,脚上的凉鞋就被沥青粘住了。我用力地想提起来,谁知脚和凉鞋一下分开,一只脚站立不稳,光脚踩在沥青上,烫得我又赶紧提起,脚底火辣辣地疼,脚掌却沾了几丝沥青。我欲用另一只脚站立,却身形不稳,自行车也跟着摇晃。我怕晃倒自行车,压扁泡沫箱,挤烂冰糕,便顾不得脚底火辣,赶紧稳住身形,扶稳自行车,勉强走到了公路对面。 卖了冰糕后,我停好自行车,返身再去取凉鞋。为了不被烫,我找小女孩要了些稻草铺在公路上,边铺边走,直铺到被粘住的那只凉鞋边。我试图用手提起凉鞋,凉鞋却与沥青紧紧相拥,仿若一对生死不离的恋人。我手上使劲,加大力气拽,却扯断了鞋袢,鞋底还粘在沥青上。最后,我只得弯下腰来,使劲抠出底板,再踩着稻草一步步走回公路边。 小姑娘见了我的狼狈相,咯咯地笑个不停,绿豆沙也顺着嘴角流了出来。不过,小姑娘心地善良,她居然带着我去到她家里,借给我烧红的火钳,补好了凉鞋。 补好的凉鞋不但破旧,穿着也不舒服。没过几天,我向父母申请后,用卖冰糕挣来的钱,买了一双新凉鞋。 新凉鞋穿在脚上,精神倍爽,就连那一天的冰糕也特别好卖。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责 编 钟 斌 主 编 陈广庆 策 划 胡万俊 重庆晚报夜雨版面赏析
|
本站论坛的文章由网友自行贴上,文责自负,对于网友的帖文本站均未主动予以提供、组织或修改。
本站对网友所发布未经确证的商业宣传信息、广告信息、要约、要约邀请、承诺以及其他文字表述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等不作任何担保和确认。
因此本站对于网友发布的信息内容不承担任何责任,网友间的任何交易行为与本站无涉。任何网络媒体或传统媒体如需刊用转帖转载,必须注明来源及其原创作者。特此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