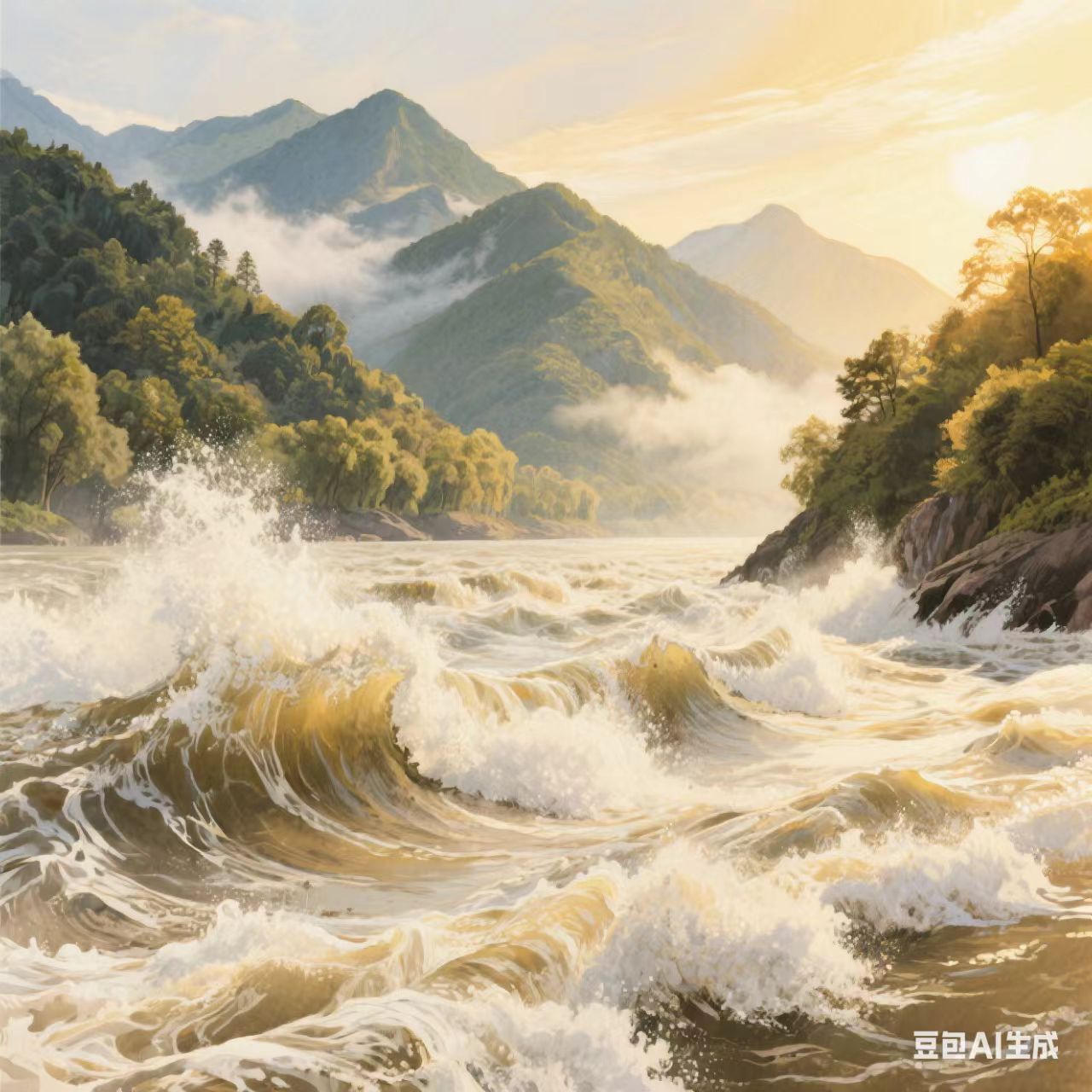夜雨|阿坚:赤子之心 如愿山河 ——读阿蛮《嘉陵十卷》
|
赤子之心 如愿山河——读阿蛮《嘉陵十卷》文/阿坚即便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眼里的嘉陵江,多停留于两江汇的朝天门。或许还知道是从合川流到北碚,其他未必知晓。 阿蛮不然,他舅舅生活在合川,他青少年时期就多次登钓鱼城,俯瞰山下的嘉陵江,心中有了问号——“嘉陵江的奔流行程,仿佛一首规模宏大的交响诗,尾声在此,它的序曲、主题和变奏又怎样呢?”
1983年,我第一次走宝成铁路。从车窗望见崇山峻岭间流淌的江水,我问列车员。她淡然答之:嘉陵江噻。此时,列车已行驶了一夜半昼。在远离重庆的大山深处,懵懂地望见家乡的流水,我很惊讶:怎么可能?这真是嘉陵江吗? 阿蛮踏访嘉陵江走到源头时的兴奋与雀跃,我能感同身受。“我从嘉陵江入长江处走来,这源头活水让我感受到一条河的伟大,离不开无数这样的涓涓细流……心中不免激动难抑,于是拿起照相机,一阵狂拍。”岂料,踩上松动的石头,一个四仰八叉摔入水里。人未摔伤,相机却不听使唤了。阿蛮并未沮丧,反而乐观:“母亲似乎也有心开个玩笑,让我以孩提时代的方式与她亲近,水源之痕由此铭刻在心。” 恰是这般乐观与豁达,让七旬的阿蛮在秦巴腹地,辗转火车、班车、出租车、乡村公交、摩的三轮和村民的运货皮卡,徒步羊肠小道,跋涉多重山峦,一次次,抵达嘉陵江引领的那些水源尽头,圆满完成对一条大河流域,从源头至终点的地域、人文、历史的踏访与考察。 我与阿蛮相识数十年,从《宁厂》《三峡古镇》《渝城九章》到眼前的《嘉陵十卷》,阿蛮始终秉承其治学严谨的风范,既遍览相关的典籍文献,又走进山野,走近江河,一路与先贤们交谈。有思辨的火花,有发现的惊叹。从而寻找那把钥匙——为何一条嘉陵江,分段谓之“漾水、故道水、西汉水等”?争论千年的“嶓冢导漾,东流为汉”的“汉”,究竟是指汉江还是嘉陵江?唐代画家吴道子所绘的《嘉陵江三百里山水图》,是嘉陵江的哪一段?巴人助武王伐纣,从哪条路穿越秦岭去牧野?嘉陵江最长的支流白龙河水的源头在哪里…… 阿蛮的《嘉陵十卷》,应是一部现代版的陕、甘、川、渝的《水经注》,丰富了郦道元的记述。《水经注》里,竟然没有嘉陵江一词,而以“汉水”称之。跟着母亲河的脉搏一起跳动,阿蛮以跨越时空的眼光,深切地感受:“嘉陵江,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条蓝线,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和鲜活的当代故事。” 秦岭之脊,巴山之崖。在密林蓬草间,在深潭石缝处,那些叮咚跳跃的水滴,那些咕咕涌冒的水花,交融而成潺潺之小溪。阿蛮掬水而饮,耳畔又传来郦道元之语:“微涓细注,若通幂历,津注而已。”秦巴山腹深处,这些名目繁多的溪水径流,从东西南北,以其各自的姿态,欢唱着、跳跃着,汇入大河之中。嘉陵江啊,便拥有了母亲的胸怀,日夜不停地滋养着她的儿女。我们对大自然的律动,对一切生命的孕育与壮大,肃然起敬。 《嘉陵十卷》,是阿蛮的又一部力作。虽引经据典,生僻字也不少,但并不艰涩。诙谐风趣的叙述,读来津津有味。引人如登山巅,尽览云霞之壮丽,沧浪之奔勃。 阿蛮这位独行侠,一路寻觅,也一路思考:从古至今,嘉陵江是怎样流过巴蜀百姓的心田?这条大河在华夏文明进程中,演绎了哪些可以承续的故事,哪些可以镌刻的人物,哪些可以重现的场景? 阿蛮与那些带路村民的交谈;出租车司机,餐馆旅店老板,寄寓一宿的房东,给阿蛮讲述的站儿巷镇的由来;一位离散老红军的故事……阿蛮充满情怀的叙述,像摆龙门阵一般,读来亲切且印象深刻。 跟着阿蛮的步履,我也兴致勃勃地在崇山峻岭间云游。流经1345公里的嘉陵江,蜿蜒此山彼岭,宁静时,它眺望斜峪、五丁、阳平、天雄诸关隘;咆哮时,它劈开灵官、药崖、明月、朝天诸峡口……奔流汇入长江,直达东海! 我想,阿蛮的《嘉陵十卷》,除却置于书案,也可放进旅行爱好者的背包,作为指南,引导我们游历祖国的山河。 (作者系重庆铁路作家协会副主席) 编 辑 陈广庆 策 划 胡万俊 重庆晚报夜雨版面赏析
|
本站论坛的文章由网友自行贴上,文责自负,对于网友的帖文本站均未主动予以提供、组织或修改。
本站对网友所发布未经确证的商业宣传信息、广告信息、要约、要约邀请、承诺以及其他文字表述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等不作任何担保和确认。
因此本站对于网友发布的信息内容不承担任何责任,网友间的任何交易行为与本站无涉。任何网络媒体或传统媒体如需刊用转帖转载,必须注明来源及其原创作者。特此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