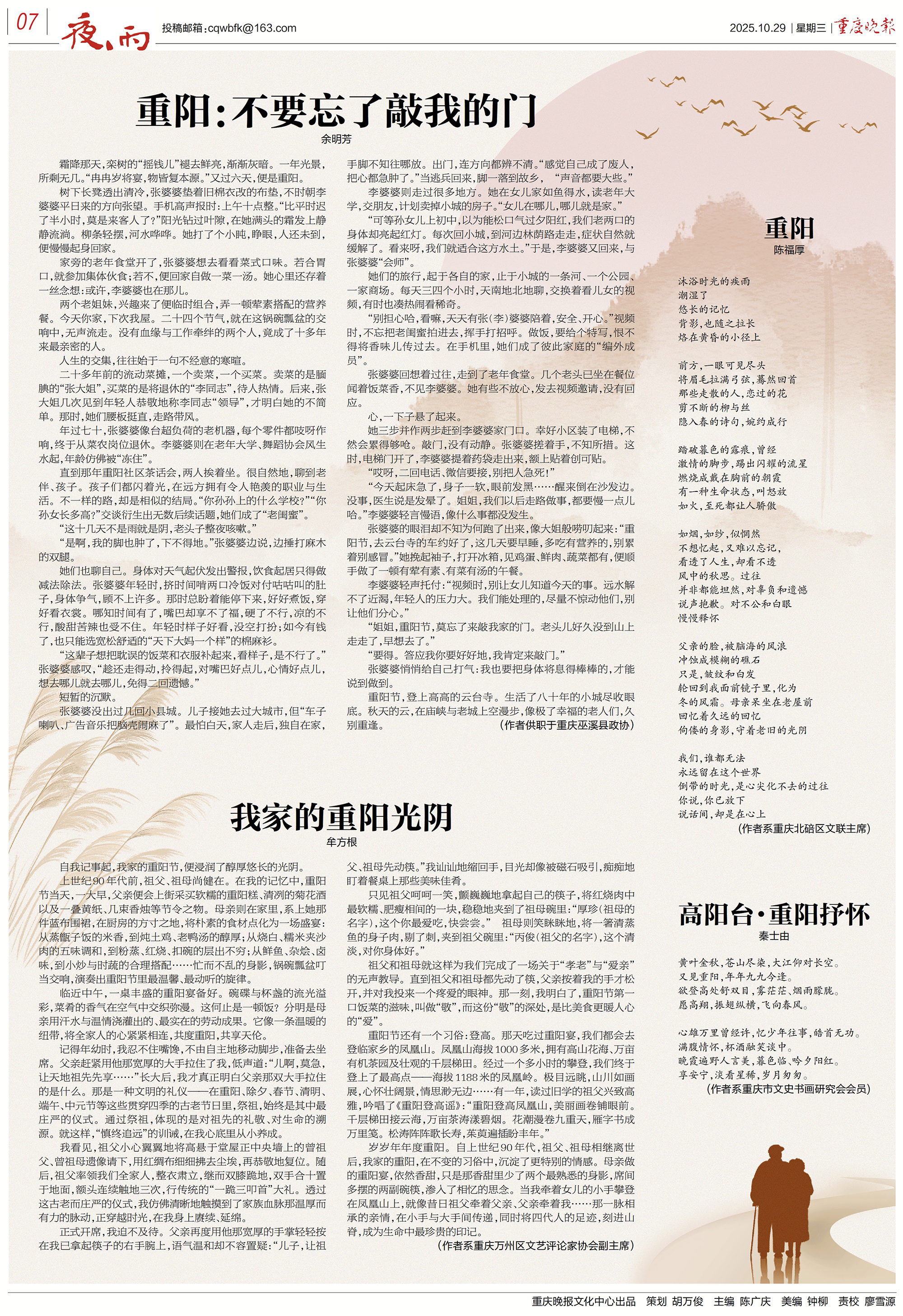夜雨|牟方根:我家的重阳光阴
|
我家的重阳光阴 文/牟方根 自我记事起,我家的重阳节,便浸润了醇厚悠长的光阴。 上世纪90年代前,祖父、祖母尚健在。在我的记忆中,重阳节当天,一大早,父亲便会上街采买软糯的重阳糕、清冽的菊花酒以及一叠黄纸、几束香烛等节令之物。母亲则在家里,系上她那件蓝布围裙,在厨房的方寸之地,将朴素的食材点化为一场盛宴:从蒸甑子饭的米香,到炖土鸡、老鸭汤的醇厚;从烧白、糯米夹沙肉的五味调和,到粉蒸、红烧、扣碗的层出不穷;从鲜鱼、杂烩、卤味,到小炒与时蔬的合理搭配……忙而不乱的身影,锅碗瓢盆叮当交响,演奏出重阳节里最温馨、最动听的旋律。 临近中午,一桌丰盛的重阳宴备好。碗碟与杯盏的流光溢彩,菜肴的香气在空气中交织弥漫。这何止是一顿饭?分明是母亲用汗水与温情浇灌出的、最实在的劳动成果。它像一条温暖的纽带,将全家人的心紧紧相连,共度重阳,共享天伦。 记得年幼时,我忍不住嘴馋,不由自主地移动脚步,准备去坐席。父亲赶紧用他那宽厚的大手拉住了我,低声道:“儿啊,莫急,让天地祖先先享……”长大后,我才真正明白父亲那双大手拉住的是什么。那是一种文明的礼仪——在重阳、除夕、春节、清明、端午、中元节等这些贯穿四季的古老节日里,祭祖,始终是其中最庄严的仪式。通过祭祖,体现的是对祖先的礼敬、对生命的溯源。就这样,“慎终追远”的训诫,在我心底里从小养成。 我看见,祖父小心翼翼地将高悬于堂屋正中央墙上的曾祖父、曾祖母遗像请下,用红绸布细细拂去尘埃,再恭敬地复位。随后,祖父率领我们全家人,整衣肃立,继而双膝跪地,双手合十置于地面,额头连续触地三次,行传统的“一跪三叩首”大礼。透过这古老而庄严的仪式,我仿佛清晰地触摸到了家族血脉那温厚而有力的脉动,正穿越时光,在我身上赓续、延绵。 正式开席,我迫不及待。父亲再度用他那宽厚的手掌轻轻按在我已拿起筷子的右手腕上,语气温和却不容置疑:“儿子,让祖父、祖母先动筷。”我讪讪地缩回手,目光却像被磁石吸引,痴痴地盯着餐桌上那些美味佳肴。 只见祖父呵呵一笑,颤巍巍地拿起自己的筷子,将红烧肉中最软糯、肥瘦相间的一块,稳稳地夹到了祖母碗里:“厚珍(祖母的名字),这个你最爱吃,快尝尝。” 祖母则笑眯眯地,将一箸清蒸鱼的身子肉,剔了刺,夹到祖父碗里:“丙俊(祖父的名字),这个清淡,对你身体好。” 祖父和祖母就这样为我们完成了一场关于“孝老”与“爱亲”的无声教导。直到祖父和祖母都先动了筷,父亲按着我的手才松开,并对我投来一个疼爱的眼神。那一刻,我明白了,重阳节第一口饭菜的滋味,叫做“敬”,而这份“敬”的深处,是比美食更暖人心的“爱”。 重阳节还有一个习俗:登高。那天吃过重阳宴,我们都会去登临家乡的凤凰山。凤凰山海拔1000多米,拥有高山花海、万亩有机茶园及壮观的千层梯田。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攀登,我们终于登上了最高点——海拔1188米的凤凰岭。极目远眺,山川如画展,心怀壮阔景,情思渺无边……有一年,读过旧学的祖父兴致高雅,吟唱了《重阳登高谣》:“重阳登高凤凰山,美丽画卷铺眼前。千层梯田接云海,万亩茶田漾碧烟。花潮漫卷九重天,雁字书成万里笺。松涛阵阵歌长寿,茱萸遍插盼丰年。” 岁岁年年度重阳。自上世纪90年代,祖父、祖母相继离世后,我家的重阳,在不变的习俗中,沉淀了更特别的情感。母亲做的重阳宴,依然香甜,只是那香甜里少了两个最熟悉的身影,席间多摆的两副碗筷,渗入了相忆的思念。当我牵着女儿的小手攀登在凤凰山上,就像昔日祖父牵着父亲、父亲牵着我……那一脉相承的亲情,在小手与大手间传递,同时将四代人的足迹,刻进山脊,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印记。(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编 辑:戴林 美 编:钟柳 主 编:陈广庆 策 划:胡万俊 总值班:杨飞 重庆晚报夜雨版面赏析
|
本站论坛的文章由网友自行贴上,文责自负,对于网友的帖文本站均未主动予以提供、组织或修改。
本站对网友所发布未经确证的商业宣传信息、广告信息、要约、要约邀请、承诺以及其他文字表述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等不作任何担保和确认。
因此本站对于网友发布的信息内容不承担任何责任,网友间的任何交易行为与本站无涉。任何网络媒体或传统媒体如需刊用转帖转载,必须注明来源及其原创作者。特此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