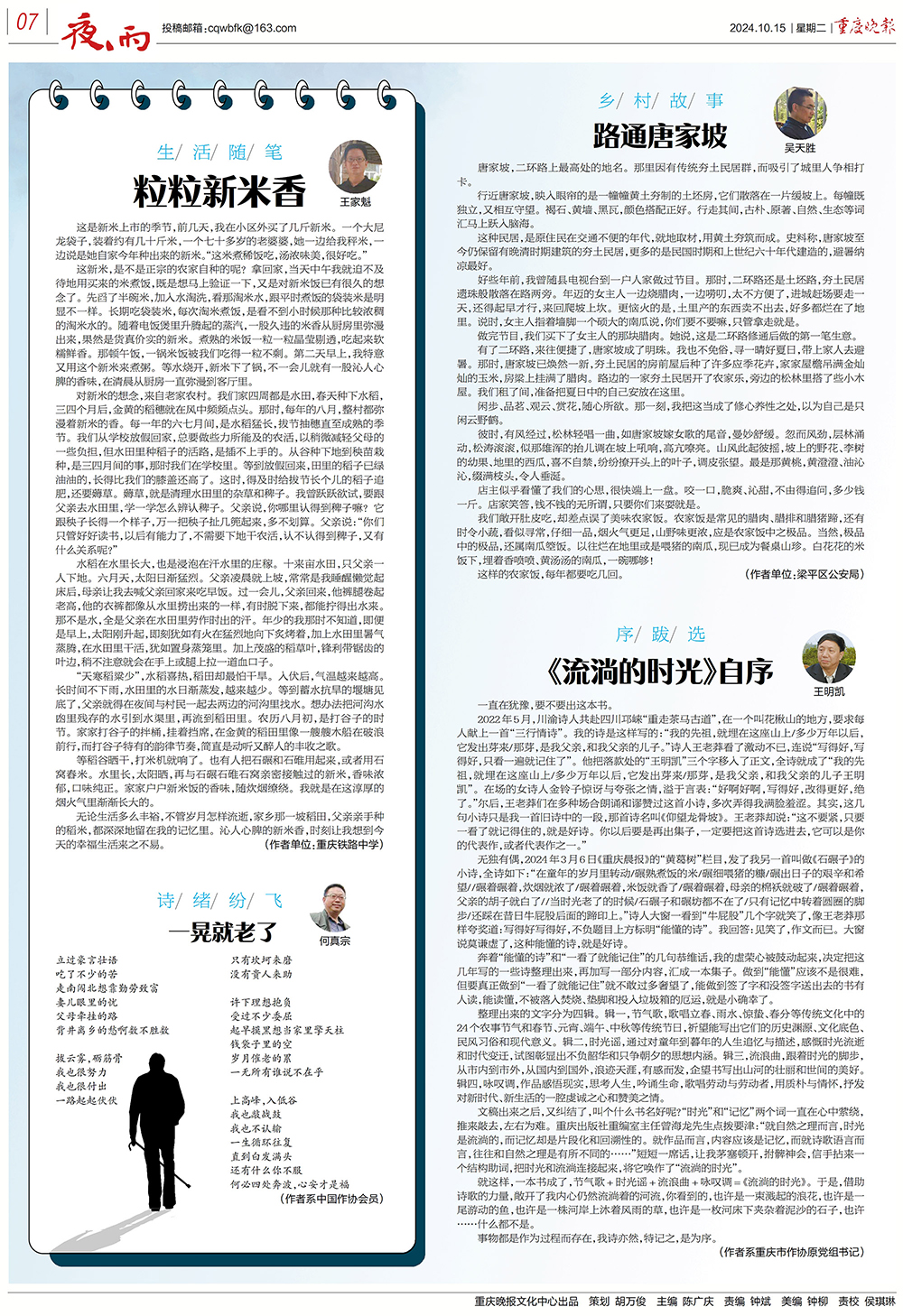夜雨|王明凯:《流淌的时光》自序
|
《流淌的时光》自序 文/王明凯
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出这本书。 2022年5月,川渝诗人共赴四川邛崃“重走茶马古道”,在一个叫花楸山的地方,要求每人献上一首“三行情诗”。我的诗是这样写的:“我的先祖,就埋在这座山上/多少万年以后,它发出芽来/那芽,是我父亲,和我父亲的儿子。”诗人王老莽看了激动不已,连说“写得好,写得好,只看一遍就记住了”。他把落款处的“王明凯”三个字移入了正文,全诗就成了“我的先祖,就埋在这座山上/多少万年以后,它发出芽来/那芽,是我父亲,和我父亲的儿子王明凯”。在场的女诗人金铃子惊讶与夸张之情,溢于言表:“好啊好啊,写得好,改得更好,绝了。”尔后,王老莽们在多种场合朗诵和谬赞过这首小诗,多次弄得我满脸羞涩。其实,这几句小诗只是我一首旧诗中的一段,那首诗名叫《仰望龙骨坡》。王老莽却说:“这不要紧,只要一看了就记得住的,就是好诗。你以后要是再出集子,一定要把这首诗选进去,它可以是你的代表作,或者代表作之一。” 无独有偶,2024年3月6日《重庆晨报》的“黄葛树”栏目,发了我另一首叫做《石碾子》的小诗,全诗如下:“在童年的岁月里转动/碾熟煮饭的米/碾细喂猪的糠/碾出日子的艰辛和希望//碾着碾着,炊烟就浓了/碾着碾着,米饭就香了/碾着碾着,母亲的棉袄就破了/碾着碾着,父亲的胡子就白了//当时光老了的时候/石碾子和碾坊都不在了/只有记忆中转着圆圈的脚步/还踩在昔日牛屁股后面的蹄印上。”诗人大窗一看到“牛屁股”几个字就笑了,像王老莽那样夸奖道:写得好写得好,不负题目上方标明“能懂的诗”。我回答:见笑了,作文而已。大窗说莫谦虚了,这种能懂的诗,就是好诗。 奔着“能懂的诗”和“一看了就能记住”的几句恭维话,我的虚荣心被鼓动起来,决定把这几年写的一些诗整理出来,再加写一部分内容,汇成一本集子。做到“能懂”应该不是很难,但要真正做到“一看了就能记住”就不敢过多奢望了,能做到签了字和没签字送出去的书有人读,能读懂,不被落入焚烧、垫脚和投入垃圾箱的厄运,就是小确幸了。 整理出来的文字分为四辑。辑一,节气歌,歌唱立春、雨水、惊蛰、春分等传统文化中的24个农事节气和春节、元宵、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祈望能写出它们的历史渊源、文化底色、民风习俗和现代意义。辑二,时光谣,通过对童年到暮年的人生追忆与描述,感慨时光流逝和时代变迁,试图彰显出不负韶华和只争朝夕的思想内涵。辑三,流浪曲,跟着时光的脚步,从市内到市外,从国内到国外,浪迹天涯,有感而发,企望书写出山河的壮丽和世间的美好。辑四,咏叹调,作品感悟现实,思考人生,吟诵生命,歌唱劳动与劳动者,用质朴与情怀,抒发对新时代、新生活的一腔虔诚之心和赞美之情。 文稿出来之后,又纠结了,叫个什么书名好呢?“时光”和“记忆”两个词一直在心中萦绕,推来敲去,左右为难。重庆出版社重编室主任曾海龙先生点拨要津:“就自然之理而言,时光是流淌的,而记忆却是片段化和回溯性的。就作品而言,内容应该是记忆,而就诗歌语言而言,往往和自然之理是有所不同的……”短短一席话,让我茅塞顿开,拊髀神会,信手拈来一个结构助词,把时光和流淌连接起来,将它唤作了“流淌的时光”。 就这样,一本书成了,节气歌+时光谣+流浪曲+咏叹调=《流淌的时光》。于是,借助诗歌的力量,敞开了我内心仍然流淌着的河流,你看到的,也许是一束溅起的浪花,也许是一尾游动的鱼,也许是一株河岸上沐着风雨的草,也许是一枚河床下夹杂着泥沙的石子,也许……什么都不是。 事物都是作为过程而存在,我诗亦然,特记之,是为序。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原党组书记) 责 编 钟 斌 主 编 陈广庆 策 划 胡万俊 重庆晚报夜雨版面赏析
|
本站论坛的文章由网友自行贴上,文责自负,对于网友的帖文本站均未主动予以提供、组织或修改。
本站对网友所发布未经确证的商业宣传信息、广告信息、要约、要约邀请、承诺以及其他文字表述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等不作任何担保和确认。
因此本站对于网友发布的信息内容不承担任何责任,网友间的任何交易行为与本站无涉。任何网络媒体或传统媒体如需刊用转帖转载,必须注明来源及其原创作者。特此声明!